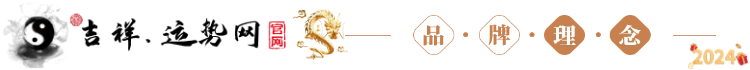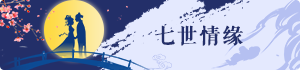我是一个心理医生,在市区中心的写字楼开着一家小小的诊所,最近,我的诊所里来了一个奇怪的女病人。
在以往的三个月里她一共来找过我15次,每次她总是很安静地坐在我的对面,小口地喝着我沏的速溶咖啡。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什么话都不说,就这样静静地坐着,她的样子很文弱很有教养。通常她会在她认为合适的时间站起来,从钱包里抽出一张百元纸币递给我。也不知道我的诊所里有什么能令她感到安慰的东西,虽然她说的很少,却一直按时排期就诊。
自然,她不是到我这里来喝咖啡的,而是来医病的。据她讲,有一个缠绕她多年的梦境令她无比困扰,但是不知为什么她就是不肯透露梦境的内容。我分析,这个不断重复的梦境必定源于她的一段不堪回首的恐怖记忆,而这段经历直至今日她也没有勇气面对。事实上大多数心理病患都源于童年时的糟糕经历。一个合格的心理医生,是不会逼着患者对自己吐露心声的,因为逼迫下得到的信息多半与事实有所出入。
在最先的几次中,我诱导性地先聊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,比如天气,比如房间装潢,比如食物的好恶。然后再引入正题。
但是此举对她并不管用,每每在说到正题时,她就开始沉默不语。
这个女病人的确令我有束手无策之感。
今天,她来得比往常要晚些,一直披散的长发用一根别致的仿古发钗束在脑后,露出了标准的瓜子脸和白皙的颈。身上穿一件用银线绣着羽毛图案的白色桑蚕丝长裙,腰身掐得很细,裙摆处有精致的银色荷叶边,她的脚很小大约也就36码,穿一双米色的夹趾凉鞋,细细的鞋带一直缠绕到小腿上,衬得她的腿无比修长。
站在敞开的窗前,仿佛一阵风吹来她就会随风而去。我很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女人,心中生出些别样的思绪,大约女人只有到了这个岁数才能真正地美好起来,不再寡淡,不再吵闹,举手投足都带着优雅与风韵。
我照例把咖啡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问:“今天准备好给我讲你的梦了么?”
她看着我,看得很专注,然后,幽幽地说:“陈医生,如果我没有记错,今天,是我第16次就诊吧。”得到我肯定答复后,她点点头仿佛下了什么决心:“那么,我今天可能会占用您较长的时间,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排在我后面的病人。”
“不会,今天下午我没有其他的病人。”我不动声色地回答,坐回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,她低着头,我轻轻掏出手机给我的前台接待发了一条短信:请取消今日下午我所有的预约,任何来访客人与电话你一律代我应答。
随后,我关上手机,我知道,今天她大概是肯讲了,我们将这种行为称做“破冰”,而隔离开外界干扰,对于“破冰”的病人来说非常重要。
女病人抿了抿嘴唇,似乎不知道怎么开始讲述,她略显尴尬地笑了一下,轻声问:“陈医生,你梦见过自己想念的人吗?”
“自然,这种经历谁都有过。”我很认真地说。
此时,她抬起头定定地看着我,眼睛如水般清澈明亮:“是吗?但是一定不会是像我这个样子。”
“我先讲个故事给你听吧,你大概会感觉乏味,不过好在,它很短。”她轻声说。
“我不会。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忽然间变得极温柔,那几乎都不像我自己的声音了。
她停顿了一会儿开始讲述:应该从我上初中的时候说起吧,我喜欢上一个男生,看得出他也喜欢我,虽然彼此没有说破,但是我们经常在不为人注意的时候交换一个绵长的眼神,没有多久,他向我表白了,我们约好用每天早上晨跑的机会在一起约会。
这感情维持了很久,都没有被察觉,我们甚至天真约定,考同样的高中和大学然后应聘到同一个公司,从此永远都不分开。
就快要毕业考试的时候,有一次他等我上学,在路上我们第一次拥抱。那感觉真是好得无法形容,我们抱在一起很久,我几乎快哭了。
这时候,一个路过的老师正好撞见我们。她停下来,低头对我说:“请给我一只烟好吗?”我把烟和火机递给她。她拿在手里轻轻摩挲着却没有抽。
女病人叹息着说:“你大约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,老师如临大敌,马上停了我们两个的课。把我们分别关在两间休息室里,等待家长来领回家。那时候我害怕的只知道哭泣。我以为我会被学校劝退了,我的父母是极度古板的人,如果那样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父母赶出家门。我很害怕,怕极了。
“可是没想到两个小时后,老师和颜悦色地将我放了出去,让我回教室继续上课。
“后来我才知道,是他找到班主任老师,说是他强行拥抱了我,而当时我并没同意。”
女病人又停下来看着我,似乎想看看我对这段描述的看法。
“继续。”我面无表情地将手向她摆了摆,此时,我并不想打断她。
她似乎很无奈的样子,又接着说:“他的父母觉得很丢人,第二天就给他办了转学手续,不久连家也搬走了,我们没有找到机会告别。我心里一直恨自己的胆小,让他独自承担所有人鄙夷的目光和不应该有的指责。我想,他一定不会愿意再和我这么懦弱的人联系了,他一定会很快就忘记我了。
“可是,他搬家后不久,有天早上,我在我窗台的花盆里看见一只熟悉的黑色钢笔,是他常用的那一根。我兴奋地几乎要晕过去,原来,他还是来向我告过别了。笔一直放在枕头下面藏着,舍不得拿出来用。每次握着这只笔就觉得心里很安定。我把它看成是一个信物或者是一个承诺,我们那个关于永远不分开的承诺。
“所以我一直坚信我们还会遇到,也许,那时侯年纪太小还不明白失散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她抿了抿嘴唇继续讲述,漆黑的眸子荡起浓重的水气。
“那天,我第一次梦见他,在梦里,我家的门铃响个不停,我打开大门,他就那样出人意料地站在我的面前,脸上是令人眩目的笑容。我的心一阵狂跳,突然间就醒了。在那个初夏早上,还未梳洗的我一口气跑到他曾经住过的房子门口。看见油漆班驳的大门紧闭着,我把脸贴在充满铁锈味的门环上,眼泪无声地落下来。
“从此以后我就沦陷在这个梦里,我不停地梦见他,在各种各样的地方,我总是意外地和他相遇。场景出人意料得完美:火烧云的黄昏,涨潮的海边,落满红枫的石桥。每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一眼就认出他。那一刻仿佛所有的事都放下了,心也空了,不由自主地就要笑出来。他就这样真实地出现在我的面前,脸上的笑容一如既往,柔软温热的手包裹住我的手。
“我们聊一会儿天,我总是有很多的话要和他说。然后我问他:“你电话是多少?”他就掏出那只留给我的黑色钢笔轻轻写在我的手心里,手心有点痒痒的湿润的感觉。每当我低头要看时,梦境便在瞬间崩塌。”
泪水从女病人眼中滚落下来,是那种大滴大滴的眼泪,重重地落在她的桑蚕丝长裙上,很快就打湿了一块。
我将桌子上的纸巾盒递给她,她的样子让我忽然忘记了所有在问询中应有的流程与技巧,我觉得自己比她还要不知所措。
“你……没有试着去找他吗?”我低声问。
她擦着眼泪轻声回答:“有,毕业后我在旧同学的聚会里打听他的下落,去他的旧邻居间追寻他的新地址,甚至去老师那里问他转到了哪间学校,不知哪里生出来的勇气,在一片惊奇怀疑的目光里我固执地追问着。但是,谁也不知道,他就这样在我的世界中完全地消失了踪影。”
“你做这个梦,持续了多久?”我又问。
“15年。”她苦笑。我吃了一惊,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手,突然间在我的心脏上大力地捏了一把,我忍不住深深地吸了口气,然后侧过头慢慢将气呼出去。
女病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讲述中,并没有看见我的反常举动。
“无数次,午夜梦回的我怅然地举着双手在台灯下看了又看。
“后来我养成了在床头柜上放一张白纸和一根笔的习惯,我想也许有一天我能幸运地在看见手心的那串数字之后才醒,这样我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把它记下来。
“我是如此固执地相信,如果世界上有奇迹发生就一定会应验在这件事上。”
她讲到这里停了一下,眼神清澈无比地望着窗外,然后她接着说。
“知道吗,不久前,我真的遇见了他。我就在他的面前站着,看着他的眼睛,但是,他没有认出我。
“那天晚上我做了最后一个关于他的梦:我和一群人拥挤着前行,那是一条弯曲的小路,我们不停地走,不知道走了多久,累极了。一转弯突然看见他站在路的中央。他第一次在人群中先认出我,伸开双臂,唤着我的名字。我在离他一米远的地方停住脚步,他一声接一声地唤着我的名字,眼神忧郁。
“从未有过的巨大恐惧瞬”间笼罩了我。这一刻我的心无比得澄明,我是如此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一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梦中。
“我知道如果再往前走就随时可能醒过来。这一米的距离对于我和他来说就是天涯,我心急如焚痛哭失声:“求求你,快把你的电话告诉我啊!”
她的讲述很有画面感,令我想起了茨威格的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。
多少个长夜相思寻梦不成的无奈,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情却如泡沫般消失在对方的无知无觉里。
她望向窗外,十二楼的西窗外有一个多日不见的美丽夕阳,天空洒满橘红色的晚霞。
女人喃喃:“我一直很不甘心,我常常想如果当初我能找到他的电话……”她轻轻叹了口气,这声轻叹在我的心里搅起了一个小小的涟漪,甚至涌上了一种非专业的惋惜。多年以来她独自沉迷于这些梦境,早已分不清现实与虚幻的界限。每当有了快乐或伤心的事她都会在梦里与他分享,在梦里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,他们不止一同长大而且一直相爱!
“我总是告诉自己,已经过去了。但是……”我看见她忽然间地又泪盈于睫。
我缓缓地说:“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,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弃。”
“也许你说的对。”她看着我:“我本来不想说给你听的。”
“那为什么又说了。”我有些探寻地看着她。
“今天早上,我答应了一个男人的求婚。”她抬起头,看着我的眼睛。“他等了我三年,今天,我决定嫁给他。”
“恭喜,恭喜。”我微笑着说,顺手拿起桌子上的茶杯想喝一口,却发现杯子里没有水。
“我要找的人已经完全地忘记了我,我找了他15年,所以我给了他15次认出我的机会,但是他没有。”她的声音里有种很绝望的东西,那语气冷冷的,如同冰凌。
我点点头:“那么只有一种可能,就是他根本没有把你放在心上,男人通常会忘记他们认为没有用处的一些记忆。”
“是吗?”她问。
“是的。”我点头。
房间里是令人窒息的寂静,女人眼中的悲伤,如同无声的雷,震得我浑身发麻。
“也许吧。”很久之后,女人忽然低声说。“这个,我想送给你。”她从书包里小心地拿出一个小木盒。
“我不再需要了,如果你愿意,请替我保存它。”
我接过木盒,没有打开也没有说话。说实话,我接那东西的时候,很费力,感觉如同接过了15年的光阴,无比沉重。
女病人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又停留了一会儿,忽然间她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,站起身向着门口走去。她没有和我说再见,我想,她大概永远不会愿意再见到我了。
脚步匆匆,如同逃离,从后面看,她的肩膀很瘦弱,没有这个年纪女人应有丰腴,就像个十几岁的女孩子,没错,她仿佛还是那个扎着简单的马尾,一说话就脸红的女孩子……
这一刻眼前的女人与记忆中的女孩忽然间完美的合二为一。
心头一阵尖锐的痛楚,一种按耐不住的想要追赶过去冲动骤然袭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