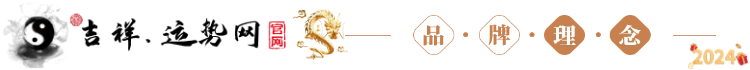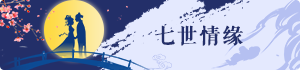真情毁于怀疑,灾难始于背叛。
一一题记
我觉得我要死了,我的意识有点开始模糊了,我努力的想把眼晴睁开,可是我觉得上下眼睑怎么那么沉呢,真的想用手帮它们一下,把眼睛掰一条缝出来……
但我依然能感觉得到蛇毒就像千万条长长的、如发丝般细细的小虫沿着我的血管一点一点的爬动,它从我的毛细血管进入到我的小静脉、中静脉,不断地向大静脉汇集,直逼心房;它还沿着我的淋巴液到处扩散,我能清晰地感觉得到它们的蠕动。
我隐约的听见腿上的血顺着那一道道被划开的皮肉向下滴嗒,那声音好远好远,如同死神的召唤,我进入迷糊的状态,如同做梦一般。
我看见她从远处向我走来,脚下踩着云彩,她呼唤着我的名字,手里还领着我们的儿子。
她走得好轻盈,好鬼异,好像飘着,走着走着,儿子不见了;走着走着她越来越小,越来越小,最后变成了一条小蛇,对,就是那条咬我的小蛇。
小蛇在果树丛中爬行,最后隐藏在某片落叶下面,再也不见了踪影。我穿着一双拖鞋,在树叶丛中轻快的行走,完全不知道树叶下面隐藏的危险。
这儿是北方,北方的秋天已经略微有点凉意了。我们这地儿很少有蛇,毒蛇更是不常见,所以当这个花不溜秋的小家伙狠狠的在我的脚跟部咬上一口时,我被这突然的问候吓得魂飞魄散。
好在我足够冷静,我迅速的抬脚将它甩了出去,然后抽出腰带扎住了脚踝关节处。
我急匆匆的叫了一辆出租车向医院驶去。北方蛇少,被咬的概率少,所以没有专门的医院,也没有专业的大夫。医生看看那两颗小小的牙印,用消毒药水抹了抹,说,回去吧,没事,咱们这儿哪来的毒蛇。
我拿出手机,给出租车司机拨了个电话,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等着。这时,我的同学一一该医院的内科主任,恰巧经过,他看了看我的伤口说,是毒蛇,抓紧住院!
毒蛇!那不是我要死了吗?
难道是她幻化成蛇来报复我?
我静静的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恍恍惚惚中好像又回到了过去……
那年,我在读大学,汉语言文学专业,师范院校。喜欢的院校,酷爱的专业,正值风华正茂,年轻燥动的心幻想着在学院雅静的环境中发生一点浪漫的事情,否则不是青春的浪费吗?
瞧我这样子,武大郎一般矮锉粗短的个子,却偏偏梦想着一位高挑的姑娘,也对,从遗传学的角度上考虑,矮子要想改变遗传基困,不得找一个高个子的配偶。
我这么瞎着琢磨着,低头行走在校园后面的林荫道上。只听见"咚"的一声,我的头撞在了一棵树上。
我正晕晕乎乎抚摸着露血丝的额头,这时一股青春的女孩身上特有的体香袭来,我如一只敏感的狗,用力的吸了吸鼻子。
"怎么样,没事吧?"
声音温柔而甜美。
当我睁开眼睛,看见一位个子高挑健美却面若黛玉的女孩站在我面前,我抬起头,恰好平视到她鼓起的双峰,那被运动衣紧箍的双峰一起一伏,像是揣着两只兔子。
我好想伸出手去,抓住那两只跳动的兔子。我怎么会有这么猥琐的想法呢?我努力的甩了甩头,让自己恢复到清醒的状态。
从此,我们相识。
可是自卑的我只能靠写诗来表达我的爱意,她激发了我的灵感,我把最美好的诗句全写在一个笔记本里,一‘个学期下来居然不知不觉写了整整一本。
她和我同一所大学,体育系,专攻长跑和篮球。而我除了爱好文学,体育锻炼也是弥补我武大郎个头的一个途径。
在遇到她以后,我往操场去的更频繁了,总是制造巧合与她相遇,我让她指导我篮球技巧,我和她并肩跑步,我疯狂的为她写诗。
临近毕业,当我把厚厚的一本专门为她写的诗集塞到她手里的时候,她发亮的眼睛充满了柔情,我知道我的爱情梦就要启程了。
毕业后,我们相约进了同一所学校教学,我教语文,她教体育,那时我们是学校最让人羡慕的一对幸福的小恋人,所有的朋友都刺激我们,说她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,我是赖蛤蟆吃上了天鹅肉。
可不是吗,我和她走在一起,整个一武大郎和潘金莲的感觉,这种感觉里含着幸福和骄傲,也带着我的自卑和怯懦,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。
那一天,终于在新婚之夜发生。当我猴急猴急的向她神秘的部位冲击,完事儿,却没有我要的梅花朵朵,我质问她,她说可能练体育的缘故,含混其词也说不清楚。
从此,我变得冷漠。
第二年,儿子出生。怀孕的时候她还在上体育课,挺着尖尖的肚子居然敢在鞍马上翻来跳去。
孩子出生时,她一下子窜上了产床,猴子一般,几分钟的时间,一只"小猴子"便顺利的出生了。我问医生,她是不是生过孩子,怎么那么好生。
说什么呢,可能是平时跟她练体育有关,孩子又小。医生非常生气。
孩子的出生,把我们拉回到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状态,我们不冷不热的日子在孩子的闹腾中也勉强过得下去。可是,我怎么感觉这个孩子不像我呢?
后来,为了多赚钱,我便停薪留职,开了一家婚纱影楼,兼搞文艺创作,在老家又承包了大片的土地,种植葡萄、桑树等,钱包一天天的鼓起来了。
她继续在学校边带孩子边给学生上课,我回家的次数随着我金钱的增加越来越少。
偶尔一次,突然造访学校,看见她如当年我第一次见她那样,穿着紧身的运动衣在操场上跑步,胸前的那两只兔子干瘪了很多,再也没有那么鲜活可爱了,我也没有了那种想抓住她的感觉。
我楞愣的站着,远远的看着她,她身边还有一年轻高帅的小伙和他并肩跑着,两人说说笑笑,甚是亲密,依如当年大学的我们。
我扭头走了,从此更少去学校了,也很少回家,回到家也是无休止的质问、争吵,然后她睡床,我也就睡了沙发,即使她多次想上我的沙发,我也没有了欲望。
冷战令我们越来越远。
我在不久的一次文友聚会上,认识了一单纯漂亮的女孩,从此我们双宿双飞,浓情蜜意的走在了一起。
我们办理了离婚手续,儿子由我抚养,她一身轻松的走了。
后来,听说她抑郁了,再也上不了课。
再后来,听说她走了,在一个无人的夜,死在了我们大学的操场上,用绳吊着,吊在当年我碰头的那棵树杈上,怀里揣着一本诗集,诗集的扉页上写满了我的名字。
再后来,我总是做梦,梦见她变成了一条蛇,每天噬咬我,一致于我神情恍惚,也抑郁了。
那天,我依然恍惚着,就穿着拖鞋走进了我的果园,便莫名其妙的被一条小蛇咬了。
我躺在病床上,迷迷糊糊似乎听见医生说,快快,抗蛇毒血清来了……
此时我看见一条会飞的小蛇离我而去,奔着我们的大学方向飞去……
也许我该去看看她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