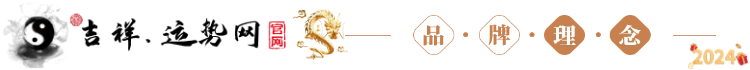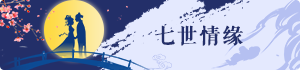大哥在眺望南山。柯小刚 图
小时候读“悠然见南山”,一直以为陶渊明的南山就是我们老家的南山头,后来才知道应该是有名的庐山。不过,后来去庐山讲学,感觉还真是蛮像,都是秀出南斗、北临长江的山川形势。山气,飞鸟,登临所见,都似曾相识。
我的老家在鄂东南,说的却是赣语,建筑也曾有耸起的山墙。族谱记载,祖上是在明朝的时候从江西迁来的。更早的渊源,可能要追溯到春秋吴泰伯、虞仲。先是越灭吴,柯姓南迁,所以至今多在福建、台湾;后来楚灭越,先人又西迁。三国时,孙吴曾建都武昌。那时的武昌并不在今天的武汉,而是鄂州。灵溪诸乡里一直到民国还属鄂城,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划归大冶。乡人明鹏先生考证说,孙吴时期的“武昌山”就是南山。
民国时期的灵乡地图。图片来自豆瓣
我的祖先就辗转播迁在这楚山吴水之间。每读唐人诗句“寒雨连江夜入吴,平明送客楚山孤”,就不禁联想到这些遥远的家族历史。明代迁到南山头的时候,先是住在深山里的“柯近溪”(讹音“柯金鸡”),后来才逐渐下到山下丘陵间的平畈。小时候还曾随父兄深入南山,寻访柯金鸡。古村早没了人烟,只剩些残垣断壁,掩没在古木荒草中。旁边有极幽深的岩洞,也曾进去探险。光影明灭,犹如读史。
南山头是横亘在南天的世界尽头,承载着家乡人民全部的传说和梦想。就连一风一雨,都是从山头望来的。从小我们就学会望山气,辨风雨。尤其是夏秋季节,如果远远望见山头的云气,就要赶紧收回禾场上晒的谷子,动作稍慢就会淋雨。看谷子不被雨淋鸟吃,看鸡不被鹞鹰吃,打猪草、赶鸭子,这些是我小时候的基本职责。
这种老房子已经不多了。柯小刚 图
父亲常讲,日本鬼子来的时候,全村老小带着鸡犬遁入深山。有的牲口进山就失踪了,成了野猪野牛。有一次避兵祸,全村都上山了,唯独我曾祖太公舍不得家业, 怕鬼子糟蹋,要在家留守。还有邻居一个大婶,也选择了勇敢守卫。结果我曾祖幸免于难,大婶却被鬼子糟蹋致死。这都是父亲小时候亲见的历史,说来令人悲愤。 彭德怀、王震、伍修权(伍是南山南麓的阳新人,我家在山北)都曾在南山头打过游击,村里有处老宅现在还挂有“大鄂政权遗址”的牌子。妈妈生前常称道大哥小的时候,带他上山打柴,看见豹子,他装作没看见,从容语于母亲:“伊(妈妈),我们下山吧。”读大学的时候,我在图书馆古籍库看到清代官修的《大冶县志》,还有老虎从山上下来,县里人家闭户三天的记载。
我的童年,冬天跟大人上山淘苕(刨捡遗漏的红薯),挖大树兜(树根);春天有漫山杜鹃,花瓣可以吃;夏天缘溪而上,忽然碰见一坡盛开的野百合;秋天松树落了叶子,跟姐姐一起上山扒松针回家做柴火。茶苞(茶树的叶苞,后来再也没吃过)、毛桃、鸡矢梨和山楂,是春夏秋三季父母从山背打柴回来,孩子们最嘴馋的期盼。 这样年复一年就到了我上高中的时候,要离开南山到县城读书,家里也搬到靠近乡镇的地方做豆腐。后来上大学,读研,工作,辗转城市,我的南山愈来愈远了。曾经生养我的土地,变成了一张春运的车票。
老家庭院(这房子是父母在八十年代做豆腐盖的)。柯小刚 图
读大学的时候,有一年寒假我没有买到票,不能回家过年。在冰封的宿舍窗下,我梦见自己走在回家的路上,遇见父母兄弟,喜不自胜。而当眼角瞥见那道深蓝的远山,泪水就把我唤醒了。
又有一年冬天回老家,物是人非,见儿时的伙伴都在沿海血汗工厂做工,村里只剩下老幼病残,整日打麻将,堕入传销和“买码”的骗局。有一个邻村少年被骗入山西黑窑,五六年全无音讯,后来从黑窑“集中营”的三楼跳下,瘸着一条腿回到了家乡。那是初代打工仔的乡村,持续了二十多年。
这些年打苍蝇老虎,风气好多了。但有些东西丧失的速度,却与发展一样快。新一代打工仔从全国各地开车回来过年,从新修的高速公路直下村口。村里征收土地,开发了商品房,却大半空着,人们买了也不住进去。县城的楼盘广告也贴到了村里,各种“英郡”、“豪庭”,“生活可以很艺墅”。物质越来越丰富,生活却更加贫乏。田地被外地老板承包,山头被矿产公司炸得千疮百孔露出惨白的石灰岩。雨水冲下尘土,像是大山浑浊的眼泪。满山的松树被割得伤痕累累,流尽了松脂。
故乡。柯小刚 图
空荡荡的南山,如今只剩下一个少年翻越积雪的山岭、寻访幽兰的记忆。我高中时写过一篇作文《南山采兰》,很得意地被老师点为范本,给全班朗诵。而老师和同学们不知道的是,后来,那两株兰草在开花之后,相继都在花盆里枯萎了。最后一朵兰花凋谢的时候,花瓣相合,仿佛一只眼睛。透过这只眼睛,推开窗户,我看见了最后的南山。
(转自微信号“道里書院”:daoli-weixin,澎湃新闻获作者授权刊发。)